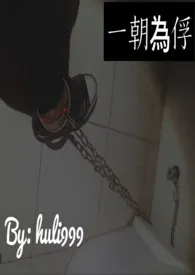朝鹤提前五分钟抵达旅馆,他没注意自己加快的步伐,上了楼,发现长廊尽头有间房门微开,是姐姐为他预留了门。
微醺的醉意,加快了血液循环,他的心情大好。
朝鹤推门而入,嘴里喊着姐姐。
无人回应。
朝鹤不恼,慢条斯理地进门,而后关门落锁的声音在静谧的空间显得清脆有声。室内昏黑,仅留床边一盏昏黄的夜灯,他嗅出空气中含杂着一股水气,果不其然瞥见浴室地板的水渍,而这些潮湿的痕迹一路蔓延至床沿。
朝鹤偏了偏脖颈,感觉上回的挠痕开始发痒了。
视线不清,他下意识去找墙上的灯,却被床上的人阻止了。
「别开灯,直接过来。」
女孩子的嗓音裹着一股蜜,好似搅不开,黏黏糊糊,全滚在喉间,朝鹤忍不住动了动喉结挤开梗在喉中的异物感。
「姐姐今天这么好兴致?」他开口才发现声音都哑了。
「别废话,要就过来。」
心里那股凶戾渗进本就肮脏的血液开始流动,朝鹤本就担不起君子之称。
他笔直地迈开步伐,顺手解了表扔在桌上,精钢落在玻璃的铿锵声让司倪暗暗打了机灵。她稍稍拉拢浴袍衣襟,心里不断给自己强心针:朝鹤不认得她!绝对不会知道她是谁!
感觉床榻逐渐下陷,司倪的心跳如雷。
平时听惯他喊姐姐,习惯他伏低的姿态,第一次发觉他其实给人如此大的压迫感。
「⋯⋯等一下。」发现对方置若罔闻,司倪防备地缩到床角,再次命令他,「我让你等一下!」
马上就要到嘴边的肉要飞了,朝鹤可不乐见,但他目前十分满意两人之间的关系,保留身份,用谎言堆砌信任,不远不近。
他现阶段无意毁坏,只好迁就。
他停下:「姐姐是欲擒故纵的高手吧,让我来,又不让我碰。」
司倪舔唇,深呼吸,说了这辈子从没想过会从她口中出来的话。「在这之前,你先把衣服都脱了。」
对方没说话。
「你不脱吗?你不脱我就⋯⋯」
「就怎么样?」
司倪听到解皮带的声音,耳朵一瞬间都麻了。
抽开皮带的声音快且俐落,司倪逐渐无法集中注意。
「姐姐说啊,要对我怎么样?」朝鹤一边挑衅,一边解开最后衬衫扣。
司倪还在思考他是如何做到半分不犹豫时,男孩子已经全裸的走到她面前了。室内幽暗,虽看不清,但能清楚感觉到对方的存在。紧张之馀,司倪硬着头皮抽出早准备好的绳索,二话不说便将他的手脚都绑在一起。
「姐姐这是做什么?」朝鹤并不反抗,反而还顺着她。「不想让我动吗?」
「你安静!」
朝鹤发现她愈不安,语气就愈凶。「我怎么又惹姐姐不开心了?」
司倪抽了丝巾直接塞进他嘴里,连带眼睛也蒙上。
嗯,好多了。
朝鹤被按在木椅上,不能动也不能说话,是有些难受,何况都还没碰到姐姐⋯⋯
她拍了两下手,准备就这样将他绑在这一整晚,明天房务来打扫自然有人救他。哼!谁让他在商佐面前乱说话!
得意之时,朝鹤忽而伸出脚,司倪就这么被绊倒在他身上,似是猜到她的想法,朝鹤顺势用双脚夹住她,司倪一瞬间无法动弹。他嘴里塞着东西,微微急促的喘息喷洒在司倪耳畔。
「你!」
见男孩子无法回答,她只得抽掉他嘴里的丝巾,刚扯开食指就被人含进嘴里,司倪不经意地叫出声,声音一出,她焦急地捂住嘴,怎么每次都会在朝鹤面前发出这种羞死人的声音⋯⋯
听见男孩子低笑,她刚恼羞,指腹就被人一点一点的含咬进口。
「你、你松嘴啊!我的手被你咬痛了⋯⋯」
朝鹤不听,反而变本加厉地舔过女孩子柔软的皮肤。司倪能感觉到他湿热的舌头压在指尖上,接着无耻的发出啜吸声。
「啊⋯⋯我不要了。」
朝鹤是真用力,不痛,但一旦司倪尝试抽离,她总觉得朝鹤这条疯狗会咬断她的手。
「姐姐,要去哪?」
男孩子的嗓子含着喧嚣的兴奋感,怀中的人软如水。
趁着司倪思绪迷离,他终于松口,好心提醒:「姐姐,我们都还没开始呢。」
本来想慢慢陪她玩,孰料她这么有能耐,现在一秒钟都不想浪费。
他哀求:「姐姐,手被绑疼了。」
「我没有绑很紧。」
「真的,妳来看是不是都红了。」朝鹤刻意扯动,司倪能听见手腕和绳索不断摩擦的声音,听上去确实很不舒服。
司倪半信半疑地靠近。
「姐姐,我不吃人。」他诱导,「再靠近一点。」
司倪觉得房间似乎变热了。
「快点,姐姐,我好疼啊。」
「知道了。」
她才靠近,男孩子便乖巧地举起被绑住的两手证明给她看,司倪偏头细看,下一秒眼睁睁地看着原先缠住朝鹤手的绳索一下子就被挣开了。
司倪错愕的同时,对方恢复自由之身,立即将人锢上腿。
她敞着两腿坐在他的腿上。「你!」
「姐姐这绑人的技巧要再多学学。」他一笑,扯开眼前的丝带,拿起地上的绳索。「别担心,弟弟马上教妳。」
男孩子的掌心很烫,伸手就往浴袍内探,司倪吓得往后缩,挪动的臀正好抵上朝鹤的敏感处,低喘声盘旋在耳边,接着她感受到有人俯身含住她的耳垂。
柔润的耳珠抿在灼热的口腔,像是要将她也含化了。
朝鹤摸到浴袍内包得严实的衣物,他低语:「姐姐,妳怎么这么不老实?」
「我没有⋯⋯」
朝鹤热心:「既然这样,我来替姐姐脱衣服。」
「不,我不需要!」她挣扎,下一刻两手被人反手扣在胸前,动弹不得。「你松开!」
「姐姐看了我的身体,我也想看妳的。」
「我没看!」
司倪是嘴硬,但更多的是无所适从,她没做过这种事,但不否认自己并不排斥朝鹤的碰触,这不合理。
「姐姐总是说这种话来气我。」
司倪看着他从容地勾起地上的绳索,接着扯开她身上的浴袍。先前跌进泥巴坑,她去洗了澡,然而朝鹤似乎误以为这是充满心机的事前准备,笑着亲暱地凑上前去嗅她身上的沐浴乳香气。
当朝鹤准备要脱她衣服时,司倪才后知后觉地想——这和预想的不一样啊!
她应该要一脚踩着朝鹤让他求饶,让他抱她大腿,说他以后不敢乱说话,什么都听她的。
「姐姐。」
司倪的脑袋很混乱。
他轻笑:「紧张吗?」
她被人禁锢在怀里,背嵴起了疙瘩,肌肤相贴,男孩子的身体滚烫。
「要不然今天就算了?」
听到这话,司倪眼神都放光了,猛然擡起头,柔软的发顶擦过男孩子的下巴。「真的吗?」
「妳亲我。」
司倪犹豫,上回夜教确实是鬼迷心窍,然而如果再来一次就是有意为之。
这两者意义不同。
「不吗?那我们⋯⋯」
司倪着急地凑上唇,刚贴上男孩子薄凉的唇时,对方似乎是知道她的小心思,反客为主,掐着她的两颊迫使她张嘴,「唔!」她反抗不及,软热的大舌直捣口腔。
接吻所发出的水渍声如同湍急的流水,冲撞两人相贴的心脏。
朝鹤使力含住女人的舌头,两人长时间无法闭阖的嘴开始渗出唾液,逐渐融为一体。他欣赏着她迷乱的神情与呼吸,即便戴着面具,他也知道她有双干净的双眼,眼尾含蜜,轻易就能勾落星辰,而他是将她亲手拽下天堂的人。
卑劣的掌控感啊,让人热血沸腾。
直到有人抚上他的脖子上的疤痕,细细描摹。
「你这痕迹⋯⋯」司倪借由微光发现套在他脖子上的绳子与他的伤疤大小吻合,但普通绳子不该勒出这样的伤口⋯⋯
「是铁炼。」
朝鹤解答了她的疑惑。
「当时去美国还小,一心想回家,寄宿家庭怕我跑,偶尔会用铁炼拴住我。」朝鹤侧过脖子,说得平静,「久而久之,就变成这样。后来大了,知道跑不了,也不会有人来接我,就也不白费力气了。」
司倪久久才吐出一句话,无法想像那是个怎么样的场景。「你的家人知道吗?」
「如果我说,这就是他们要的,姐姐会相信吗?」
母亲是酒店小姐,父母的身份是泥沼与金子的差别,而生出来的孩子便处于灰色地带。她以为他是玩世不恭,却没想过他说的话句句属实。
司倪问:「为什么是我?朝鹤你并不知道我是谁,你对我太信任。我可能对你不利,伤害你,背叛你,你给我太多机会做这些事。」
朝鹤当然想过。
「但妳从来没有,姐姐会这么想,就表示妳从不想这么做。」
⋯⋯不,她知道蓝湘私下想栽赃他,想让双方家族对朝鹤生厌,她甚至还差点成为帮凶。
没有一个人是站在朝鹤身边。
朝鹤还有心情玩笑,「姐姐,先担心妳自己吧。待会就算哭,我也不会停喔。」话语刚落,眼前的人就这么伸手主动抱住了他。